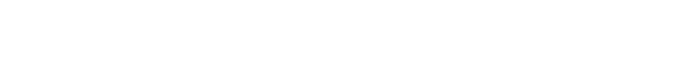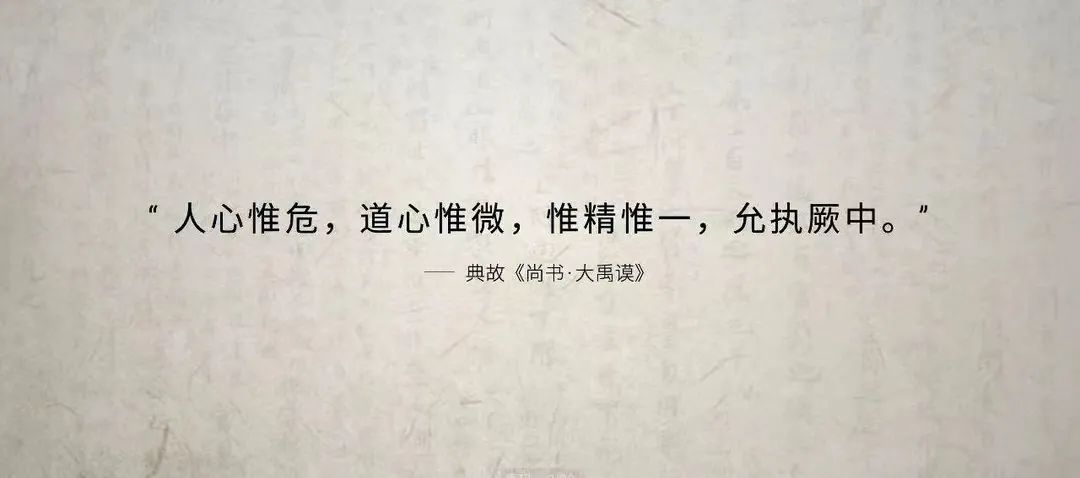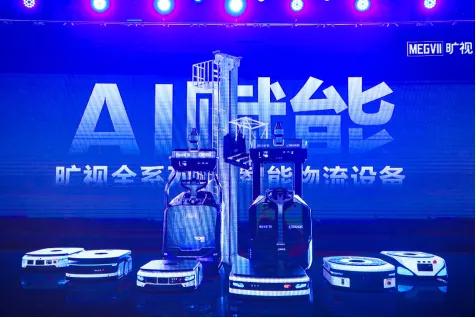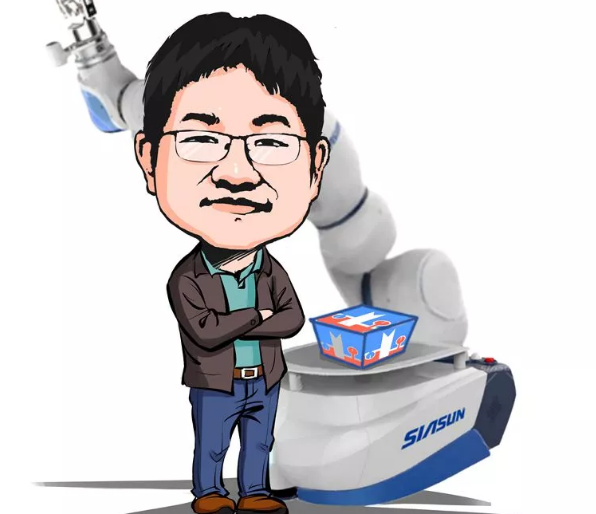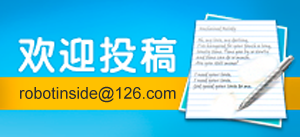面對在場媒體,施密特舉例稱:“你們都是記者,在會場還要不停地用電腦打字,而不只是聽和說。為什么不能讓機器去做比如制造業(yè)的重復工作、很多打字的工作?”他預計,在Google公布開源第二代機器學習系統(tǒng)之后,尤其是在醫(yī)療、游戲、教育等領域,機器學習將發(fā)揮巨大的價值。

機器學習背后的黑科技
機器具備學習能力究竟有多重要?Google科學研究員GregCorrado做了一個比喻:“機器學習就像火箭助推器,而大量的數(shù)據(jù)就是火箭的燃料。”
谷歌機器學習的原理是:用眾多的電腦模擬人腦中的“神經(jīng)元”,形成一個人的“神經(jīng)網(wǎng)絡”(ArtificialNeuralNetwork)。它不需要借助大批研究人員幫助電腦標明事物之間的差異,只要為算法提供海量的數(shù)據(jù),“神經(jīng)元”與“神經(jīng)元”之間的關系將會發(fā)生變化,讓數(shù)據(jù)自己說話,讓組成“神經(jīng)網(wǎng)絡”的機器具備自動學習、識別數(shù)據(jù)的能力,在新的輸入中找出與學到的概念對應的部分,達到機器學習的效果.
例如,當人們需要計算機辨別圖片內容的時候,各個人工神經(jīng)元就會把所抓取的信息傳遞給被設置為“決策者”的神經(jīng)元上,它們通過統(tǒng)觀其下層所有神經(jīng)元所呈現(xiàn)的信息,結合案例、數(shù)據(jù)的分析及算法最終得出結論。
事實上,谷歌對于機器學習的研究要追溯到7~8年前的語音技術開始。但施密特透露,機器學習這一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是發(fā)生在計算機視覺領域。
三年前,Google科學家杰夫·狄恩(JeffDean)在接受《第一財經(jīng)日報》采訪時透露,“GoogleX”實驗室通過連接16000臺計算機處理器,創(chuàng)建了一個機器學習的神經(jīng)元網(wǎng)絡系統(tǒng)。結果發(fā)現(xiàn),這個系統(tǒng)自行創(chuàng)建了貓這個概念并且自學了對貓的辨認,這就是“自我學習”。
不過,當時的谷歌機器學習還只是一個實驗項目,局限于認知類的簡單工作。幾年過后的今天,谷歌的機器學習已經(jīng)從識別谷歌應用中的語言和圖片的第一代機器學習系統(tǒng)“DistBelief”更新到了第二代的TensorFlow系統(tǒng),并且應用于Gmail、GooglePhotos、Google翻譯、YouTube等產(chǎn)品中。
Google研究員GregCorrado告訴記者,利用機器學習技術,Gmail電子郵件服務的垃圾郵件攔截率提高到了99.9%,誤報率降低至0.05%。這背后的原因就是,在垃圾郵件過濾器中引入了機器學習,這一技術能夠通過分析大量計算機上的電子郵件學習識別垃圾郵件和釣魚郵件。更重要的是,機器學習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而非只是利用預先設置好的規(guī)則攔截垃圾和釣魚郵件,它還能在運行過程中自己創(chuàng)建新的規(guī)則。
而另一個能代表這項技術的最新產(chǎn)品是,谷歌在Gmail上推出智能自動回復功能SmartReply。SmartReply是基于Google機器學習系統(tǒng),對海量郵件里的場景、郵件寫作風格和寫作語氣進行分析,從而幫助用戶篩選適合語境的回復短句。
“一小步”與“一大步”
“在Google內部,現(xiàn)在機器學習已經(jīng)是谷歌搜索中第三大重要的技術。”GregCorrado對記者說,人工智能是科學家希望機器變得更智能,從經(jīng)驗和數(shù)據(jù)中學習。“手動去編程機器顯然沒有讓它自己學習來得更有效。”
不過,實現(xiàn)機器學習的訓練過程仍然漫長。在這個過程中,機器需要做大量測試、調整和適配工作,也很有可能犯一些人們不大可能犯的錯誤。
這也正是Google把機器學習系統(tǒng)的大門向業(yè)界工程師、學者和擁有大量編程能力的技術人員敞開的原因,希望業(yè)界將TensorFlow實現(xiàn)各種各樣的機器學習算法,同時也為其在各種場景下的應用帶來改進。
“例如,計算機的視覺如果比人更好,為什么還要人去開車?應該讓機器開車。現(xiàn)在是醫(yī)生看X光,未來如果讓機器看是否會做出更準確的診斷?”施密特說,“在開源之后,如果全世界的聰明人都將給Google很好的回饋,Google會有更好的發(fā)現(xiàn),讓產(chǎn)品和服務更完美。”
他同時提到,機器學習非常善于預測時間先后順序的事件的發(fā)生,自己尤為看好機器學習在醫(yī)療、游戲、教育等領域發(fā)揮的價值。“甚至我們競爭對手的團隊都會用它,這就是谷歌不同于別人的原因。”
對于目前Google機器學習的開放策略,GregCorrado表示,一方面,Google開放機器學習,在于鼓勵大家從不同角度去研究,即使在Google內部,也不只是一種方法去做機器學習;另一方面,Google已經(jīng)和學術界、企業(yè)界、不同的實驗室合作,例如Facebook、百度等。
他同時認為,機器學習并不是魔術,不要盲目地認為機器學習就一定比沒有機器學習的好,它只是工具,能夠讓研究人員轉化他們瘋狂的創(chuàng)意,而不需要他們重新編寫代碼。
不過,當機器能夠像人類大腦一樣去思考時,究竟該如何看待機器學習的倫理問題?未來機器人是否會像電影《少數(shù)派報告》中那樣,充當“壞人”的角色?
施密特給出的回答是,“只有電影里才會把機器人設定成壞人,在現(xiàn)實世界里,可以通過算法制定一些規(guī)則來保證它能夠正確地工作。”